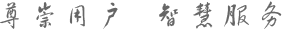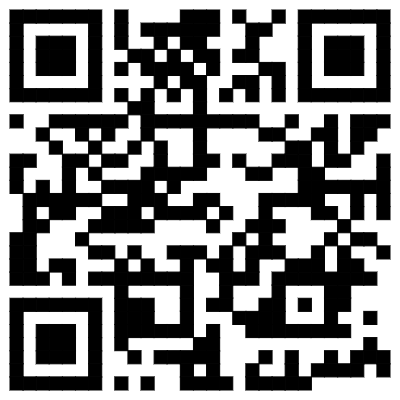关键词:
城市
文学
唐代
洛阳
建筑景观
唐诗
摘要:
本选题主旨是从唐代洛阳城的公共建筑景观和私家建筑景观来论述洛阳城与唐诗的关系,其基本内容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从城市的标志建筑景观来分析洛阳与唐诗的关系。
标志建筑景观之一是总体和细节意义上的“洛阳道”(含“洛阳桥”)。“洛阳道”自古便是一个包含特定意义的意象,出现在历代文人的歌咏之中。它与城市生活诸多世象譬如良马高轩、游侠少年、王孙佳人、清歌艳曲等等紧密联系,体现出城市的种种典型特征。在唐代亦然,它是一个最为全面地展示人生百态的场所景观。第一个观察点是城外“洛阳道”。它是四方往来的各条陆路、水路,它将城外四方怀有各种欲望的唐人引向道路尽头的欲望之城。洛阳以良好的地理位置成为一个具备经济优势、政治优势的城市,那些喧嚣浮华的城市表象之下有着各种欲望可能达成的结果,天下来者皆有机会,或有可能获得不同的成功,故竞趋者也众,呈现形象也繁。当然城市无法满足所有到来者的欲望,于是城市的失意者也顺着“洛阳道”四散而去。这其中既有未尝获得过成功的彻底失意者,同时也有已经获得成功却中道被贬谪出城的失意官员。有唐一代这些连接欲望的“洛阳道”屡经朝代变迁而车马不息,最能折射唐人内心世界。
第二个观察点是城市之中的“洛阳道”。这些城中道路是城市之中的重要生活场景,它是城市之中具有公共性的建筑,使城市之中属于不同生活层面的居民得以联系,得以交叉,成为这座城市具有代表性、景观性的场所。本文选取了洛水之上,连接洛阳南北两段城区的三座主要桥梁天津桥、中桥、浮桥加以叙述。这其中又以坐落在城市中轴线上的天津桥最为著名。洛阳桥在容纳展现城市人生百态的同时,也成为城市盛衰的一个标志。
标志建筑景观之二是洛阳城中以及洛阳城市圈中的“洛阳宫”。城中偏西北的“上阳宫”是与附近的天津桥孪生的城市地标性建筑景观,它是唐洛阳城中主要的宫院建筑,其位置在皇城之西,面临洛水。于是外郭城中的居民和来到洛阳城的人们都常常能够得见其丽制。“上阳宫”以其伟丽的形制成为唐人浪漫诗歌想象的一个主要对象,而帝王的驻留是否决定了它的盛衰,那些吟咏上阳宫的诗歌作品反映出这一宫殿的变迁,也同时反映出城市和时代的变迁。
唐代直到玄宗朝洛阳与长安是并为两都的。唐诸帝常常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于是沿途往往多设有行宫。这些行宫在唐代属于河南道,同时在唐人的理念中,这些洛阳附近周围的行宫已然与洛阳合为一体。于是本文以“城市圈”的概念将其包括其中,作为“洛阳宫”的一部分。这些唐行宫随着国策国运的变化也盛衰相继。唐人对它们的关注多在中唐和晚唐。此时它们成为中晚唐文人凭吊惨淡时局,缅怀盛世不再的对象物,成为盛世残余下来连接过往的“断片”。本文选取了最为有名的兰昌宫、连昌宫、绣岭宫加以论述。
标志建筑景观之三是城市之中的“洛阳楼”,主要是出现在唐人诗文之中的“五凤楼”。此楼地处方位在文献中众说不一,结合唐人诗文可大致考其位置在城市中轴线上端门附近。在唐人的目光中,此处不仅是城市登临的绝佳视点,同时也是帝王举行与民同乐的“酺宴”所在。这种公共性建筑是与王朝权力和政治用意紧密相连的,既可对内渲染盛世繁华,也可用来向这个国际都市中的域外来者展示国威。
标志景观之四是洛阳城中以及附近的“洛阳寺”。洛阳作为中土佛都滥觞于后汉,其后在唐代之前又有曹魏、西晋、北魏、隋定都洛阳,其间洛阳随着各朝君主宗教观之异或呈现出浮屠宝塔林立,或呈现出佛寺伽蓝凋坯的状态来。这些随着佛教西来伴生的建筑既容纳了这种异域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显示出这种意识形态在中土的接受轨迹,并目睹了这座城市发生的各朝演义。唐代的洛阳佛寺建筑是佛教东传来到中土兴盛第二次高峰的见证,其背景是则天皇后欲借助佛教的力量称帝,于是在武后时期的洛阳,佛寺的兴建乃至命名莫不受到其影响。在“安史之乱”中的洛阳佛寺也不免浩劫。中唐武宗灭佛的政令又使洛阳佛寺被大量摧毁。于是洛阳佛寺在唐代宗教与政治关系的莫测变化中,在唐王朝的风云突变的命运中,都打上了浓重的时代标识。此外佛寺以其清嘉的地理位置和清雅幽静的氛围使唐人多好往来寓居宴游于其间。唐人在此多有吟咏,这些诗歌将宗教精神与时代之感熔铸一体,因此在唐代诗歌史上,洛阳佛寺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景观。
这些城市的标志建筑景观的意义在于它们将这个城市乃至这个时代的命运雕刻其中。本文试图以传统的城市文学研究中“强调城市之于作家的经验性”的思路,从“文学再现城市”这个角度来考察城市建筑景观与城市文学(诗歌)之间的联系,进而考察这种联系对城市的意义。
下篇是从城市的私家建筑景观角度来分析洛阳与唐诗的关系。
这一部分主要以即唐代洛阳分司官员的私家园林为切入点,以这些官员在这些“场所”之中的文学活动为主要考察对象,来研究城市与文学,城市建筑景观与文学之间的联系
 万方期刊
万方期刊
 CNKI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CNKI期刊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详细信息
 万方学位论文
万方学位论文
 CNKI学位论文
详细信息
CNKI学位论文
详细信息
 CNKI学位论文
详细信息
CNKI学位论文
详细信息
 万方期刊
万方期刊
 CNKI期刊
详细信息
CNKI期刊
详细信息
 CNKI期刊
详细信息
CNKI期刊
详细信息